由乡长带队,政府和镇派出所都来了不少穿制服的。他们软硬兼施。派调解员,七嘴八舌劝从王艳家那头来的这些人。肖世豪是事后才派人被从学校接回家来的,村民们在吵吵嚷嚷,闹哄哄的气氛中,这才开始听到一些人嚎啕大哭。亲戚也在哭!
“伤心和痛哭终于让一些人冷静下来。”
“那么,好好睡会儿。别打扰她了。”
好像她还活着似的,真的稀奇古怪。有人替她轻轻盖好被子,动作实在有些诡异。
“不安排人供饭?”那个人问。
“差点就忘了。”有个家伙伸长脖子说。
其实在场的人,有一小半都并非是真正血亲。从那边来的不少人大声舞气叫喊饿了,像演出。又仿佛,并不是声称的来讨公道,亲戚本身就是来亲戚家吃酒的,顺理成章。寨上那些帮忙的人这才恍然大悟,纷纷动手淘米煮饭,取下火塘上炕的现成腊肉和血豆腐,割回来一大堆的莲花白,勒下把木姜花做糊辣子蘸水,大伙儿就在地坝上弄吃的。开始杀猪。地坝和堡坎脚路边都烧煤炭火,他们估计是安起心要把肖家存煤和干柴这次全搞完。
他俩还是在针叶林阳光屋。
“不吃饭,你抱我睡觉。”肖世豪哀求。
“睡不着的!”他说。
(反正,我肯定是要让他们带走的。
外婆对许多舅舅大声舞气说,这是什么人家,豪儿继续呆在他家,一准儿学坏。
死了的人离去不远,都还在门板上看着。
亡魂不会安安静静地走开的,事完不了。
这种鬼地方,连点人情味都没有!我姑娘在的时候如何对待他们,现在,她可以说尸骨未寒,而旁人又怎样待她的。寒心!
叫肖世豪必须永远记得这些家伙。
留在肖家确实有问题。看不惯,哪天再扯疯,又拿包耗子药再把娃娃毒死了。)
外婆说这番话的时候,突然泪如雨下,清鼻涕阴悄悄淌在她的丰满嘴唇。包括下葬的那天,肖宗俊、爷爷、叔叔,连肖世豪都没有尽心尽力,或者说花多大功夫哭,在场的村民各怀鬼胎,筒直是,外人说因为娘家来人那样闹,大家更接近表演性质。一个劲儿哭的人是肖世豪奶奶以及叔娘,也就是肖宗军的老婆。谁都不相信他会真的伤心,丈夫死了都不会;平时她可从来没少干挑拨离间那种事。肖世豪才十一岁,当年他有点置身事外,不停歇拿眼睛角角打量着这些乡间艺术表演大师。外婆家那边的人吃过酒席,马蜂窝被山火逼近似的,他们一大群人咋咋呼呼、火急火燎走掉了。肖世豪拼命挣脱舅舅的手,冲过阻拦,他并没有答应去寄人篱下。他后来一屁股坐在堡坎上地坝边,呆定定的。有只巨大的鸟从低沉天空不经意划过。可以看得出来,肖家沟父亲这边的人对男孩作出的天然选择十分满意。他身体仿佛瘫痪了一样。(我爸爸掉了一颗门牙的牙齿轻轻咬住下嘴唇。我的嘴唇跟肖宗俊其实长得特别像,一个半开叫高年级女同学曾经说过肖世豪嘴唇性感。是什么意思?后来他俩站在床边地上弯腰曲背穿裤子。
我听出话外之音来了的。抬起胳膊,电灯拉亮了,我发现,他俩正在给自己打针。包括我爸爸也在打。我站在从没刷过油漆松木桌子边。这样,又过了若干年,我忽然问陈娴阿姨,我可不可以也打一针?
他对我说,打针就是止痛。在扯谎!甚至比去县医院打都更管用。但是会上瘾。要打针,就非得作好一切思想准备。免得到时候会后悔。我才不可能上瘾,干啥事都不会,只想试试看,到底怎么神奇法。有可能超过舞台上的魔术师。那些人为什么乐此不疲。感冒药难道不是真的感冒药?经加工以后,还多出来治肚子痛的功效。
甚至,还有看魔幻片效果。
天黑尽了,对死的人,前面长路会有一盏灯。次日清晨,他俩从梦境走了出来。但还是伸手搂抱着她,让细嫩的脸颊轻轻贴着自己胸脯。先别吻着,控制不住情绪,只有再次使自己达到高潮,一股强大暖流冲了出去。然后才依依不舍地起床。)
村民们,包括那些八丈杆打不着边的妇女,突然,反而嚎啕大哭了起来。她们想哭肖世豪,因为他从此没有了娘,肯定更可怜。也有种人,明摆着就是在假装哭。然后叔叔肖宗军也同样坐在土路边排水沟的沟帮上,显得痛不欲生。他背靠着粗大的水杨树树干,哭起来样子相当滑稽。也许更是在哭他亲哥。他家都不像办丧事。
“简直就是闹了一场地震。”长舌妇说。
从那件事情以后,肖树森再没缓过气来。
“生病了,也同样恐惧打针!”
如果真的是中毒,那就打一针阿托品先保命。这样,一转眼到了年底,管教科的科长站在旗杆下的前台,面对着站成竖直一排排的学员讲话,当然也有不少戒断者。
他额头直出虚汗,声音嘶哑。不屑说,操场上哑雀无声。他是真的病了。在主席台后头三中队的办公室里,坐着从场部来的领导和干部。峨沟二大队的三个中队,包括中队长以下的干部纷纷站着,继续开会。天气实在闷热,所有人并不怀疑,恐怕很快就会下一场雨。如果下倾盆大雨这条简易马路又要断了,场长告诉大队长:
“现在,你手底下人增加了。”
“确实是有些困难。”他坚持说。
“你们现在就必须要把困难想在前面。”
路断了好啊!一断就不会再送人来了。
“现在送来劳教所的人太多了。”
没想到大队长满口应承:“那是当然!”
(我抬起头告诉医生,从小的时候就害怕打针。我们那个地方有人肚子痛,如果去医院打一针,往往刚打完,连裤子皮带都没来得及系好,他就扑嗵一头栽倒了,一个劲儿在水泥地上抽筋。后来呢,怎么样?结果他死了,死都死得让当地风声鹤唳。乡下人爱造谣!把那种精炼、提纯过的感冒药看透了。打完针总感觉种痛苦。
“有段时间会觉得不再那样孤单。”
“不害怕孤独!”那小伙补充说。
冰包括口服和鼻吸。那人狠狠心车脸问:
“你那里还有哪几种?”
“四五种规格。”同学极不情愿回答。
稍微犹豫:“我想去看看怎么提炼。”)
“听你讲的这是些什么话!”
“全体学员的伙食必须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标准来执行。不能允许有土政策。”
更不准谁贪污克扣。有贪婪心肯定犯罪。
“若出现了,立马纠正。执迷不悟一经查实,不管涉及谁,我绝不对底下姑息。”
“哪怕——就算他真的是皇亲国戚。”
“哪个敢啊!”一个中队长接话说。
“大队长,你们自己种的菜仍不理想?”
“肯定供应不上。”他回答。
老场长感到一阵阵焦虑。
“暂时不够,也不要紧。”
“有许多问题正等待解决。”教导员说。
所领导迅速作出一系列指示:“趁着路打通的时候,要派车多从外面采购一些可以存放得久一点的蔬菜。更要多找几条梁渠道,尽量多想办法,我们不能坐等。也根本不允许不作为,伸长脖子干等。尽快有思想准备,并从各中队再抽调一些比较放心的学员,最好是,每个中队都搞个蔬菜队。”“即然是,情况明摆在这里,那你们还在等什么?以为天上会掉豆渣!我本人全力支持。只要有点想法,要是没有大的问题,那就生动起来。”“也可以派人到省城采购点菜种,可以找到农业部门的专家,求人家指导一下,先看看有哪些品种更适应我们这种高海拨的山区……”
气氛变轻松一些了。政委插句话说:“也可以在学员当中选拔人才,多问问,看看有哪些原来就是种蔬菜方面的行家里手,搞得好,年底评比,真有贡献那种也可以作为他减期标准。把思路尽量放宽些!”
“就是别老古板。”场长说。
(我爸说,峨沟农场的夜间天气非常好,能够看到满天星星。我向来适应能力都比较强。即使是,在外面干单工,他最大的毛病还是喜欢喝酒。并不像谣传那样,我甚至怀疑肖宗俊压根就对毒品不怎么感兴趣。现在,好像是又有点小醉。究竟想怎么样,那就动作快点!天就快要亮了。我正好在一个窝棚里,等接头的人。生怕喝不成酒,死喝烂喝的,办正事还醉了。所以,从此我就开始打针了。怕你个头,酒精会更刺激才不信,你们分明是骗老子的吧。其实,我可能连吃药都有些担心。也许是的,早都闯过了头昏目眩,两眼乱冒金星那种前期情况。你还在一个放纵的年龄。我当然没资格指责谁,每次都心惊。
“也害怕再醒不过来了。”他说。
我确实口干舌燥的。)
“还是水源。”“饮用水方面出的问题实在太严重了。”“今年的情况,恐怕干得比哪一年都老火,连续四个月没掉一滴雨。各个大队的情况都一样,所里考虑得最多的也肯定是用水。”“峨沟大队的水供应,只能说是,确实比苦李树那地方稍微好一点。”“整个夏季应该没问题。”
“到了雨季,可能没有问题。”
“但是不从根本上解决,估计冬天,肯定了的,还是只能用拖拉机下河边拉水。”
“守着这么大一个淡水湖,居然缺水。”
“真的是叫人看我们笑话。”
“就是扬程太高了,抽不上来啊!”
“今年肯定只能想办法解决。”
劳教所新收的学员越来越多,原先预计大队只收三百名,现在已经超过了五百人,去年底苦李树大队用两台拖拉机拉水,从早到晚,根本不敢耽搁平均摊到每个人头上都不够两茶缸。当然了,苦李树位置更高,盘山公路的路况没有峨沟这边好。那点水,四合院几个伙房用水都无法保证。
(医生一直在给我排毒,就是特别口干。你需要多喝白开水。简直困死了,又进入不了梦乡。我晓得始终逃不脱。那就对无耻叛徒进行一次惩罚!那你还在找死。
所有人甘拜下风。
绝对没有人会轻言退却。
我趁着两个家伙情绪都好,盘算好应该怎么建议。没办法,那你必须要控制量。)
“现在确实不需要派人外出拉水。”“虽然说够吃,但想洗点东西,肯定还是完全不行。”“在找到新的水源之前,利用雨季,要尽可能多蓄水。”“我早跑去看过了的,而且还不止去仔细查看一次,水池开裂已经是漏的了。淌进去的水实在漏得厉害。”“我告诉场长,”老教插了一句话说,“原本计划好的,把铜鼓山流阴洞的那一股水引到大队,也不知道所里考虑得怎么样?”“你们这是打算逼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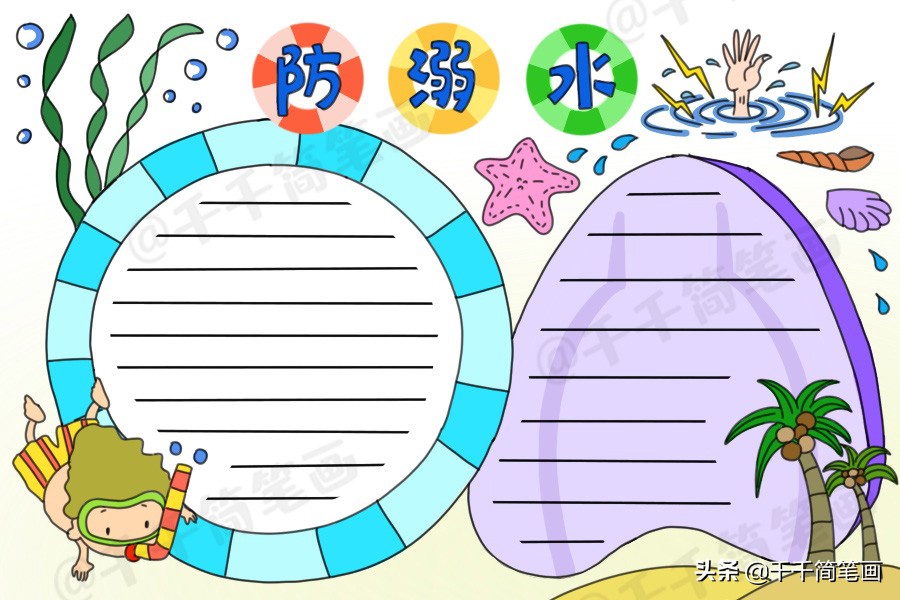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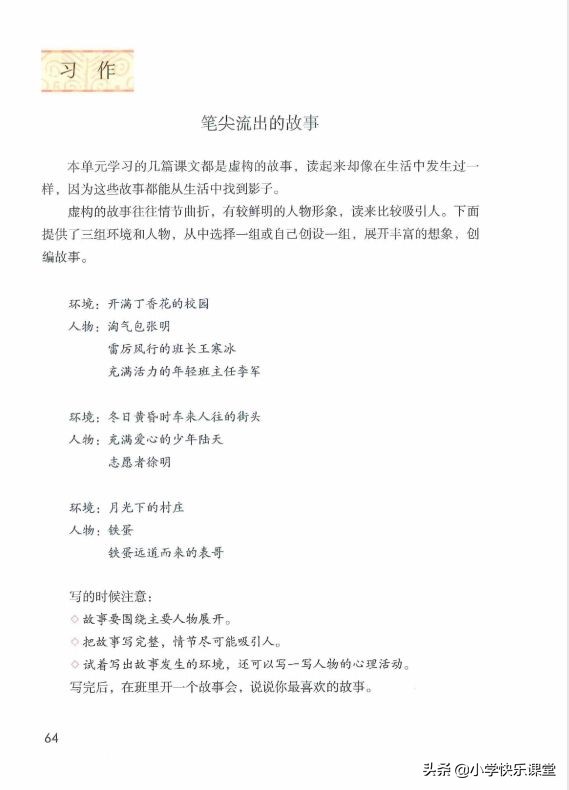
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