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网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一句来源于真实生活的话语触动了很多人的心,有人说,“世界那么大,谁不想去看看?”可是大多数人却是敢想而不敢做。从固定不变的生活模式中暂时跳出来,去另外一个环境体验新的生活,这种被称为“间隔年”的生活方式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接受。旅行、骑行、支教、读书、培养孩子……给人生“放个假”的原因也更为多样化。
“与其驻足,不如上路”
间隔年(Gap Year)是欧美国家的青年在升学或者毕业之后工作之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让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体验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还有一种“Career break”的说法,指的是已经有工作的人辞职进行间隔旅行,以调整身心或者利用这段时间去做别的事情。无论是学生还是上班族,都是在给自己“跳出来一下”的人生际遇。
天津80后女孩付哲曾在京工作,负责企业对外宣传工作。2013年10月,她因为要处理家事辞职回到天津。事情结束后,她决定陪伴家人出去散心,同时也给自己放一个假。2014年3月到2014年底的这段时间,她和家人游览了欧洲和日本。
付哲很喜欢《近在远方》上的一句话:“与其驻足,叹咫尺即天涯,不如上路,笑看天涯亦咫尺。”旅途中总是充满未知,新鲜的人和事还有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丰富了她的阅历,开阔了她的眼界,让她可以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突发状况。
骑行则是山东女孩温宇智的一个梦,而它的源头还要追溯到多年前。初中的时候,她在新华书店最爱的地理旅游书柜里翻到了一本书,叫做《裸奔》,讲的是一个法国人在中国骑车探险的万里行。于是骑车去拉萨成了她心底的一个梦想。之后,她开始关注跟骑车远行相关的论坛、书和电影,也尝试了一些短途骑行。大二的时候,她看到石敬写的一本书——《我在中国画了一个圈》。石敬是一个女人,她的国内骑行之旅激发了温宇智的小宇宙,她开始认真思考骑行所需要的条件,得出的结论是钱和时间。可惜有时间的时候她没有钱。
2011年大学毕业后她开始从事网络编辑工作,并且有了积蓄。工作时间,温宇智时常感到,新媒体行业是一个更替速度足以让人抓狂的行业,从业者总是要不断学习,力求速度和创新,可是却常常不得要领。温宇智说,她热爱单车,但她更爱文字,她希望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有温度的。她也希望这次骑行不仅是一场圆梦之旅,更能为她的文字注入活力。
2013年3月,温宇智递交了辞呈,骑着一辆普通的捷安特atx690自行车,驮着20多斤的各种装备,从家乡济南独自出发,骑过菏泽、开封、郑州、三门峡、潼关、西安,又跟沿途邂逅的骑友一起翻秦岭、过剑门关,到达天府之国成都,并从这里骑上著名的川藏线,最终到达拉萨。
与物质无关与责任有关
选择“间隔年”并非是80后、90后的专利。70后丁跃(化名)1999年大学毕业后在津工作,刚入职那几年,他几乎每隔一周就要出差,生活被填得满满当当。2003年,天津正经历“非典”,他进入疫区工作后被隔离21天,在这人生中难得“闲下来”的时间中,他翻看报纸看到了关于团中央“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的报道,“想换一个环境感受生活,想做些事情”。这个念头冒出来之后,他决定付诸行动,从5月底报名到8月培训后,他简单收拾了行装,前往广西百色田阳县南部大石山区的巴别乡中心学校开始为期一年的义务支教工作。
同事很支持他,给他买了军刀、衣服,感觉就像他要去受苦或是野外生存一样。丁跃自己心中倒没有太大落差,“我本身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当地学校和自己小时候的环境差不多。一小间房子,两层长长的木板上挤了二三十个学生并排睡觉。”但是经历了大学读书和工作几年的城市生活,丁跃也有很多不适应,他生长在北方,南方潮湿、多雨,屋子四处漏风,“我现在关节遇到天气不好时还‘咯咯’响,应该就是那时候落下的。”而且当地地处山区,缺水且水质不好,用水主要来源是雨水,但含碳酸钙太多,烧开之后要沉淀一会儿,下面一层白渣,上面一层油花儿,丁跃曾带学生到山上的蓄水池去考察过,水池里还漂着死老鼠。
当年团中央支教项目共有200多名学生志愿者、11名社会人士。丁跃和他的同伴——一位从广州宝洁辞职的女士,选择了最艰苦的地区支教,尽管当地离县城只有50多公里,但因为地处深山没有路,从县城单程坐车就要四个半小时,两车错车时需要一辆车先停下来,边上就是万丈悬崖。
条件虽然艰苦,生活却非常充实,丁跃教学生思想品德课,每个月的花销就100多元,“因为根本没有东西可买”。
教课之余,他开始思索,“当地为什么会贫穷?”为此,丁跃去家访、去调研,他试图去了解当地的农作物、人口、建设、通讯、水源,“仅靠物质援助,并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养成当地官民的依赖性。”
他也不鼓励每个学生都要走出大山,“走出来可以,还要回去,通过自身改变家乡,不然家乡就会成为空心村。”他了解数据发现,他所在初中每年都会流失两个班的学生,能考上高中的只有十三四个人,能考上大学的更是寥寥无几。很多孩子喜欢画画唱歌,家长觉得是不务正业,但丁跃告诉学生,“上大学并不是唯一的路,鼓励多样化发展。做生意挺好的,村里人吃不上蔬菜,解决吃蔬菜难题就是对父老乡亲作出贡献,喜欢画画可以帮别人盖房子搞设计,要发挥自己最有潜质的一面。”
一年间,他通过努力,帮助学校募集3万多元建设了新的食堂,募捐了价值5万多元的新书并建成了校图书室。其间,他除自费资助了10名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外,还募捐了4万多元的助学款资助了一批考上高中但上不起学的孩子。同时,他还先后联系了天津津南区的过滤水装置企业和广西当地多家知名出版社募捐图书,尝试帮助当地解决实际难题。
距离自己的“间隔年”已经整整12年,对丁跃而言,这些经历仍历历在目,他资助的学生现在仍有联系,有一位已经当了老师,他开始操心学生找对象的事情。他与当年一起的志愿者也保持着很好的友情,“有一个黑龙江的老师,有一个在成都中国银行工作,还有一个在上海做贸易工作,支教之后又回去继续做公司,收入都很高。他们包括我的共通点都是想去做点事,想有新的人生体验,没有失恋,也没有躲避社会的原因或心态。”
说起“间隔年”,丁跃认为,“这跟物质没有关系,和负担的责任有关系。年轻时,父母家庭还不用自己去照顾,没有影响别人,不违法、不犯罪,怎么去生活和别人没有关系,给自己一个空当更有利于个人成长。”但他也直言,年轻时觉得“钱是身外之物”,回来之后发现自己“爱钱”了,很多事没有钱解决不了,连身体健康都保证不了。如今,丁跃已回到原先的工作之中,妻女在旁,他们一家人依旧热爱生活、热爱自驾游。
出发时就知道要回归
付哲说她在旅行之初就清楚地知道之后要回归工作状态,所以并不是完全放下一切去放松。旅行时,她就决定回到天津工作,希望能有更多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她在旅行途中就开始着手找工作,并在2014年底找到了现在的工作。
尽管现在的她在忙碌、疲惫的时候会怀念那段轻松、自在的时光,但是在她看来,不管是旅游还是给自己放假,都是为了充实自己以更好地回到“现在的世界”,而不是逃离。她说,如果有一天萌生了“出去看看”的想法,她会在考虑过经济实力以及再次择业的情况后再做出慎重的决定。
而路上的经历则成为选择“间隔年”生活的人们一辈子的财富和回忆。骑行途中并不是一帆风顺,雪山的严寒、贵州、广西、广东段的酷暑都让山东姑娘温宇智有种想哭的冲动,有一次她还差点遇到危险。她和骑友骑到巴朗山垭口,当时气候很恶劣,他们不但没有看到巴朗云海的绝美景观,还差点因为高原反应、冰雪、极度低温和黑暗丢了小命。因为下山路上没有灯,两边也常常没有围栏,他们只好开着强光手电沿路中间的黄线骑行,一个紧跟一个,每到拐弯就大声传达口令。面罩被雨雪打落了,嘴唇和牙齿不自觉地抖动,长指手套已经湿透了,冰冷的手甚至都捏不住刹车,不住打哆嗦的腿也控制不住踏板和车身。温宇智说也许当时每个人都跟她有同样的想法,那就是如果这次能安全下山,真的谢谢老天爷了!当晚很幸运,他们在下山半途借宿到一个施工队工棚中。第二天,才顺利到达山脚的日隆镇,看到了远处美丽的四姑娘山。回想那次经历,温宇智笑说:“这都挺过来了,以后什么都难不倒我了。”
很多人说温宇智辞职的举动很勇敢,然而对她来说,这并不是勇气的问题。温宇智告诉记者,她对工作非常负责,辞职只是一个选择,但这个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考虑了间隔年后的工作问题。她说,她的生活还会继续,她依旧会努力工作,仍然会有很多梦想,和出发之前没有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是,她证明了自己的能量,有了更多实现梦想的信心。
2013年9月,温宇智骑车回到原先的工作单位,好像一切都未曾发生。温宇智说,旅途结束了,她没有舍不得,而是淡然地品味回家的感觉,只是觉得,结束是为了新的开始。
2009年,《迟到的间隔年》一书首次把间隔年这个概念介绍给国内青年人。其作者孙东纯于2006年12月1日,带着一张仅存有21000元人民币的国际银行卡,离开自己生活多年的城市,带着一个不知道可以给自己带来什么的“间隔年”主题。从原来计划的三个月走到十三个月,从原来计划的目的国印度变成一次横跨亚洲的旅途,一路上边旅行,边以义工的身份服务于非政府组织,帮助当地需要帮助的人……在路上,遇到了他当下的日本妻子。
2009年底,豆瓣网友自发组成团队,建立了间隔年旅行网。该网站致力于国内间隔年文化的推广,并且希望为义工旅行和工作旅行的青年人提供一个交流和分享的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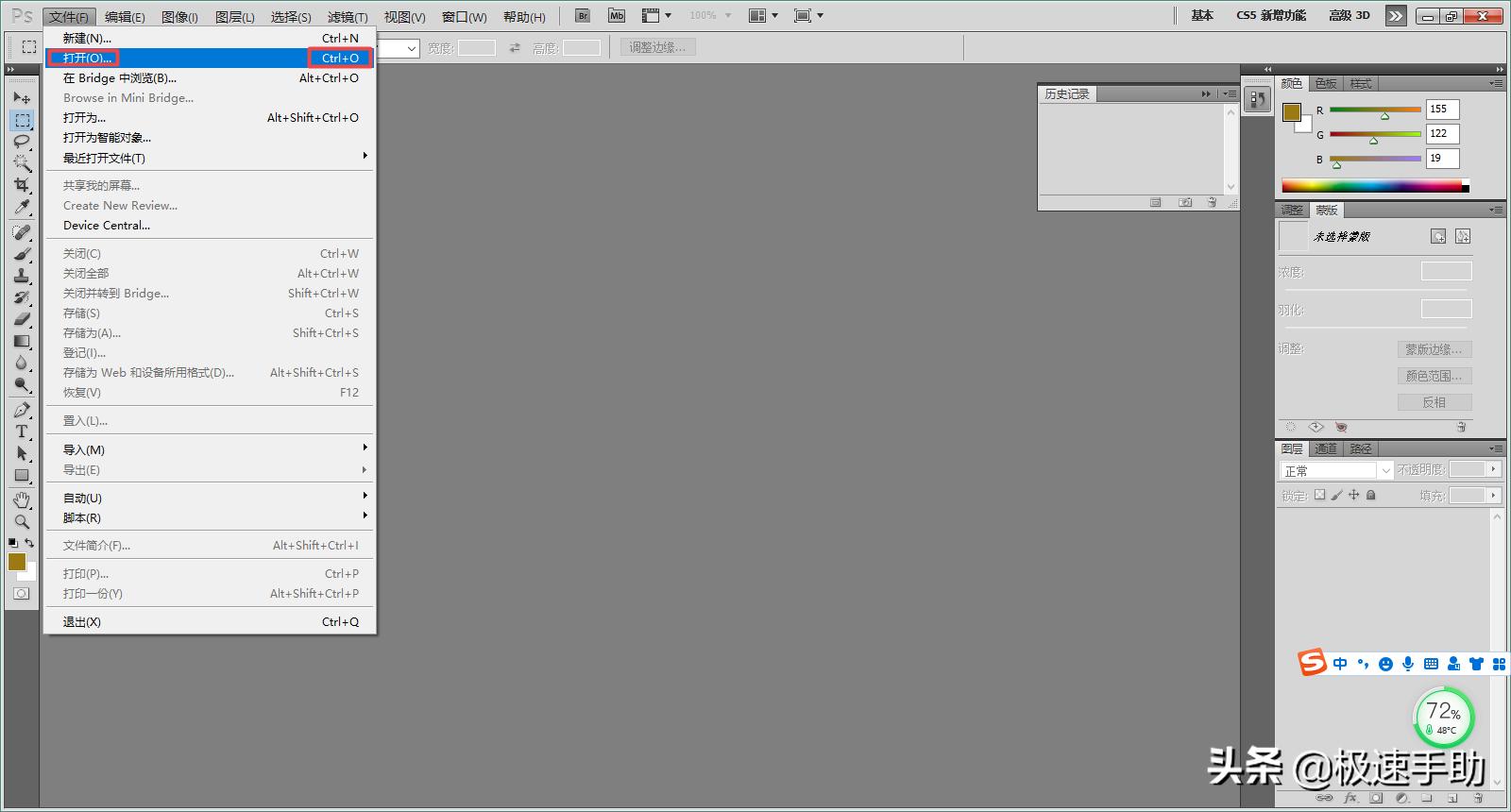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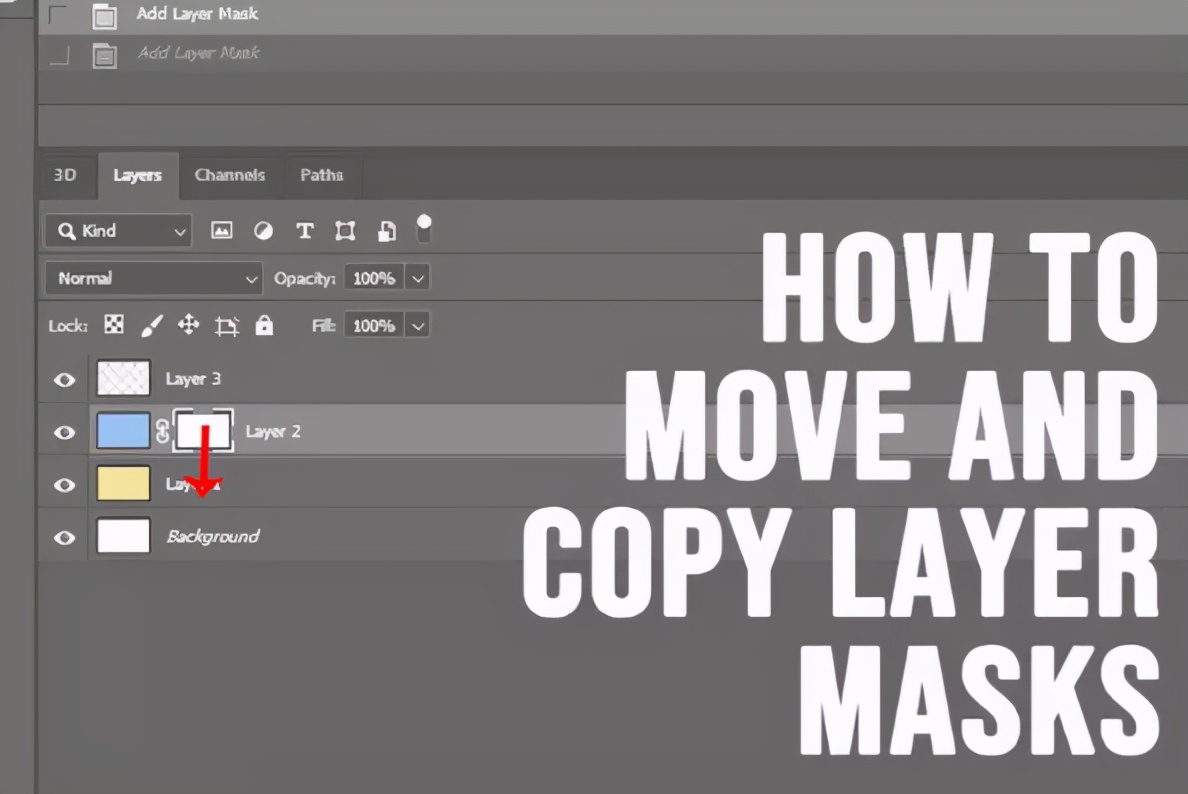

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